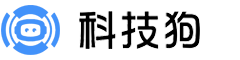李侠

今年获诺奖的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即几乎都是上世纪80年代在基础研究领域萌芽的,经过多年发展终于成熟并被学术界承认。笔者曾与友人戏言,40年的种子终于开花了,这是基础研究的胜利,更是长期主义的回报。
获奖者中颇具戏剧性的人物当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卡塔琳·考里科。自1982年博士毕业以来,她一直专注于研究信使核糖核酸,甚至为此遭受被学校解聘、降薪以及无法晋升职称等挫折。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基于其理论开发的新冠疫苗横空出世,极大缓解了疫情对于全球造成的危害。由此,她的高光时刻终于在40年的寂寥后姗姗来迟。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2020年以来她获得了无数荣誉,如今更是科学界舞台中央最耀眼的明星。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幸运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做出了伟大成果但到死都没有被承认的人。
在笔者看来,科学家个人要获得诺奖需要具备3个条件:首先,成果要绝对过硬;其次,要有人推荐或者机缘绝佳;最后,寿命要足够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
那么,产生诺奖级的成果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呢?笔者认为同样需要3个条件:首先是耐心;其次是宽容;最后是资助。这3个条件中,前两个是科研生态环境的基础性表征,后者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相对而言,耐心与宽容氛围的建设比资金投入要艰难得多,毕竟资金通过政策安排可在短期内有很大改观,但耐心与宽容的科研氛围的形成则需要非常漫长和苛刻的条件。中国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此可见,耐心与宽容是非常高级的文化格调。美国的科研生态环境被公认是非常友好的,素以耐心、宽容以及对基础研究投入慷慨而著称,但即便如此,考里科仍然面临申请不到基金、被解聘、无法晋升职称等艰难处境。
既然基础研究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发展基础研究呢?
由于我们国家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导致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产出总量严重不足。笔者曾用官方数据分析过,中国基础研究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现明显的弱正相关性,而发达国家这一数据是明显的强负相关。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成果离市场化应用还很遥远,无法带来直接收益,这部分投入只会造成经济的挤出效应。弱正相关性只能说明我国的基础研究成果供给太少,任何知识都能带来正向收益。
笔者曾分析过中美两国2000年至2020年21年间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结构。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平均占Ramp;D的17.2%,而中国这一数据仅为5.2%。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强度是中国的3倍多,美国Ramp;D总量约是中国的1倍,而中国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量约是美国的1.5倍,由此可以清晰地知道,中国的基础研究境况很严峻——人多钱少;加之现有的科研生态环境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导致中国基础研究孱弱。
当下,中国在政策层面推进基础研究遇到的最大思想阻力,就是技术与科学哪个更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科技史的视角来看,技术在短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科学更能推进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前者依托技术,后者依托科学。而20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完全是采用一种新模式——科技一体化,科学甚至显得更重要一些,近年来那些撬动社会变革的新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即便按照传统模式来决策,短期内技术更能推动经济发展,理应技术优先,但这种模式在中国也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基础研究的孱弱,中国的应用研究基本上处于无效的空转状态,值得应用转化的上游知识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大多数应用研究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
笔者曾用工业生产流程来解释这个现象——基础知识相当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技术相当于原材料的加工方,当原材料供给有限而高度同质化的加工方越来越多时,工业产品会质次价高,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加工方的恶性竞争以及内卷;相反,如果原材料供应丰富,就可以极大拓宽技术范围,并减少无效内卷状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知识更新加快,技术迭代才会随之出现,否则缺少前端的变革,技术迭代就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诺奖是一面每年照一回的科学透镜,让我们看到自身的不足与短板。这面透镜照多了,一些共性问题自然就会呈现出来。
今年这面透镜让我们再次锚定了3件事:首先,政策层面对于基础研究要坚持长期主义,加大投入力度,不能游移不定;其次,继续推进破“四唯”“五唯”,建立科研的多元评价体系,营造一个适合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最后,塑造科学建制的耐心与宽容精神。在功利主义时代,体制的耐心与宽容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味要求个体保持耐心与宽容,既是不公平的,也是无效的。知识丰腴之处,创新才取之不竭,反之,创新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